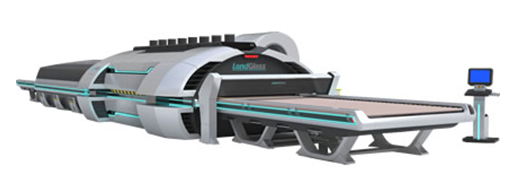人們經常把行業內體(tǐ)量、規模或市場份額巨大的(de)企(qǐ)業稱(chēng)之為(wéi)“大象”,玻璃行業曾經的民營企業老(lǎo)大(dà)——江蘇華爾潤集團有限公司(下稱“華爾(ěr)潤”)無疑是行業(yè)裏舉足(zú)輕重的一隻。2015年10月(yuè)20日,這隻“大象”的突然停產清算,雖早有征兆,但仍然帶(dài)給市場巨大的(de)震撼(hàn)和無法忽視的餘波。
有人說,華爾潤的破產拉開了玻璃行業整合的大幕,也(yě)有人說這將是玻璃行業(yè)去產能的階段性成果。毋(wú)庸置疑的是,華爾潤注定要在我國玻(bō)璃行業的發展史上留(liú)下無(wú)法抹去的重要一筆。無論是其發展壯大被時代賦予的特(tè)殊性、經營思路調整所具有的(de)代表性,還是最終(zhōng)走向衰落折射出的行(háng)業共(gòng)性問題,都值得全行業在當(dāng)前化解過剩產能、轉(zhuǎn)型升(shēng)級的重要節點,進行仔細梳理、思(sī)考和借鑒,也讓我們更加關注2016年玻璃市場走向。
同行眼中的“大象”
“華爾潤一直是我們學習的榜樣,是我們行業的老大哥。”提起當年的行業巨頭華爾潤(rùn),武漢(hàn)長利玻璃有限責任公司期貨部王成斌這樣告訴記者。而這種印象,也(yě)正是(shì)很(hěn)多同行對華爾潤的共同記憶。據(jù)資料顯示,在1981年正式進入(rù)平(píng)板玻璃製造行業之前的十多(duō)年間,華爾潤主(zhǔ)要靠“打零工”的方式加工(gōng)生產刨床等產品,後(hòu)更(gèng)名沙州玻璃廠,於1997年正式采用現名稱(chēng)。確立玻璃為主業後,伴隨(suí)著國家經濟體製(zhì)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國民經濟持(chí)續快(kuài)速發展,尤其是(shì)進入新世紀(jì)以來房地產(chǎn)行業發展的黃金年代,華爾潤(rùn)通(tōng)過產業(yè)結構升級和企業體製的(de)戰(zhàn)略性調整,逐漸(jiàn)發展成為玻璃行業巨(jù)頭,其成本管理、質量控製、銷售模式等都(dōu)被同(tóng)行作為學習(xí)標杆(gǎn)爭(zhēng)相效仿。
“2000年(nián)的華爾(ěr)潤,已經是全國玻璃界的龍頭企業(yè),其浮法玻璃產品逆(nì)江(jiāng)而上能賣到湖北市場。”王成斌說。這種強勁的市場銷售能力,折射出的正是華爾潤通過規模化(huà)發展降低(dī)產品成本帶來的競爭優(yōu)勢。提到華爾潤當年的規模化發展,就有同行將其描述為“占盡天時地利”。一方麵,國家經濟體製(zhì)改革為民營企業(yè)的快(kuài)速發展帶來了機遇(yù);另一方(fāng)麵(miàn),在房地產快速發展的黃金(jīn)年代,玻(bō)璃行業曾(céng)一度成為暴利行業,而其主要產能又(yòu)集中在對玻璃產品需求量最大、需(xū)求結構多元化的長三角地(dì)區,其快速銷售產品的優越性不言而喻(yù),市場規(guī)模隨之持續快速擴大。
“曆史上我國最大(dà)的兩個玻璃加工基地就是珠三角、長三角,這兩個地方要玻璃要得(dé)最多。貿易商隻要能弄到貨,到了7、8月把倉庫放(fàng)開,價格就是一通暴漲。”回想起當(dāng)年浮法玻璃的市場銷售,武漢長(zhǎng)利玻璃有限責任公(gōng)司董事兼副總經理張山高如是說。
華爾潤也牢牢地抓住了這個行業需求膨脹的特殊時期,在巨大經濟效益的推動下加大了擴張的腳步,並將(jiāng)這一戰略基調延續到了後(hòu)期。最終形成了一個浮法玻璃生產線達20條(張家(jiā)港本(běn)部(bù)10條(tiáo),廣東江門(mén)3條,山(shān)東巨野4條,河北(běi)遷安2條,遼寧大連1條,合計年(nián)生產能(néng)力約8760多萬重量箱),旗下9家子(zǐ)公(gōng)司,業務範圍遍布玻璃深加工、矽質原料生產、鹽化(huà)工、油化工、煤化工、物流等多個領域,注冊資本達4.58億元的龐大玻璃巨頭企業。
2000年(nián)和2004年,華爾潤通過兩次企業轉製成為一個產權清晰、以玻璃生產(chǎn)為主業的股份製民營企業。截至倒掉(diào)之時,華爾潤總資產達90多億元,合計總負債約65億元,其中銀行貸款50.9億元(張家港市本部銀行貸款27.6億元),除對下(xià)屬(shǔ)子公司擔保6000萬元外,無(wú)其他對(duì)外(wài)擔保。
同行(háng)對於華爾潤快速發展的評價(jià),一如其官(guān)網介(jiè)紹所說(shuō):華爾潤集團在國家改革開放後的發展曆程就是我國玻璃工業快(kuài)速發展的一(yī)個縮影。
盲目擴張不可取轉型升級是王(wáng)道
一家如此累累碩果的巨頭企業何以一夕之間破產?當記者問及造成(chéng)“大象”倒掉的原因時,業內同行的回答或委婉或直接,但矛頭直指以下幾個方麵:罔顧行業現實逆(nì)市建線;輕易涉足行業外其他領域;經營(yíng)不(bú)善,負債過多致資金鏈最終斷裂。 “近年來華爾(ěr)潤新建產能過多,最終狀況正是其盲目擴張帶來的後果。”河北正大玻(bō)璃有限公司期貨部(bù)經理莊自朝對記者(zhě)表(biǎo)示。
莊自朝所(suǒ)說(shuō)的(de)“盲目擴張”,尤其體現在2008年全球金融(róng)危機爆發後(hòu)。房地產行(háng)業需求萎縮帶來的全行業大(dà)麵積虧損及以後一段相當長的時期,華爾潤未及時調整產能部署,依舊以產(chǎn)量(liàng)求生存。據2008年2月新聞顯示,華爾潤當時計劃總投資27.6億元於(yú)山東巨野建設4條700t/d生產線、玻璃深加工中心和一個(gè)30萬噸煤焦油精(jīng)煉基地,但是最終隻(zhī)建起(qǐ)了(le)4條線。
2009年9月(yuè),國務院將平板(bǎn)玻璃列為6大產能過剩的(de)行業之(zhī)一;同時,平板玻璃由於高耗能、高汙染的特點,被國家列為治理大氣汙染的主要行業。即便如此,華爾(ěr)潤的“擴張”戰略仍未止步。而這種盲目(mù)擴張,實際也(yě)是同時期很多(duō)未看清行情逆轉現實、未走上(shàng)轉型升級道路企業的共同短視之處(chù)。
業(yè)內人士表示(shì),在下遊需求進一步萎縮、全行業產能進一步擴張帶來行業低利(lì)潤的現實前,華爾潤發展所依靠的中低端浮法玻璃產品單一、附加值不高(gāo)、競爭力不強(qiáng),越來越(yuè)難以支撐(chēng)起龐大的公司規模、員工(gōng)數量帶來(lái)的包袱,使得企(qǐ)業在產品結構調整、轉(zhuǎn)型升級,甚至最基(jī)本的環保設備改造方麵都步履維艱。
“其實一開始華爾潤玻璃口碑還是可以的,產品質量很高,和台玻、南玻質量(liàng)靠近。”一位曾經營華爾潤在江浙滬地區30%玻(bō)璃產品(pǐn)的貿易商告訴記者,“後來為了降低成(chéng)本,華爾潤在行業內首先改用石油焦、煤焦油替代重油,但更換燃(rán)料後產品質量開始(shǐ)變得不穩定,非常脆,給玻璃鋼化帶(dài)來了很大(dà)困難(nán),以至於有的加工商指定絕對不用華爾(ěr)潤的平板玻璃。”漸漸地,華爾潤玻(bō)璃產品開始被業內冠(guàn)以“中(zhōng)低端”形(xíng)容詞。
更使華爾潤雪上加霜的,是(shì)企業製定的投(tóu)資戰略屢遭失敗。
“純堿、石英砂包括物流領域的投資還算是有利潤的,因為華爾潤自身產品也要使用。”杉杉(shān)玻璃期貨負(fù)責人劉政告訴記者,“最致命的打擊,是華爾潤從2007年開始在(zài)一個(gè)石化項目上(shàng)的連續(xù)投資(zī),前後共投入了30億元,最終卻以失敗告終。”而這一失敗,也使得華爾潤另(lìng)一個耗資2億元(yuán)、研發數年的玻(bō)璃地板項(xiàng)目,僅在一次發布會後就草草收尾。
正因如此,“不要輕易(yì)涉足行業外的其他(tā)領域”也成了河(hé)北大(dà)光明實業集團有限公司玻璃期貨負責人武延民談(tán)到華爾潤事(shì)件時,向記者講出的第一個教訓。
除此之外,據劉政介紹,華爾潤還因旗(qí)下某項目平台與其合作公司江蘇匯鴻國際集團產生糾紛而對簿公堂,此後(hòu)又(yòu)因無法按時歸還(hái)貸款被江蘇銀行(háng)告上法(fǎ)庭。
“2013年(nián)後銀行對玻璃行業抽貸動作頻繁。到了2015年,一下子20億元的銀行還款壓(yā)力頂在(zài)頭上,終於(yú)壓垮了不堪重負的華爾潤。”張山高說,“這一如當(dāng)年的浙玻(bō)。現在來看,能活下來的企業都是比較少依(yī)靠銀行貸款的,所以還是要靠自己的(de)實力。”
房地產市場的黃金十年,長利也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,但其對產能擴張始終采取了克製態度(dù)。據(jù)王成斌介紹,在華爾(ěr)潤等巨頭進行大(dà)幅產能擴張的時期,長利(lì)毅然謝絕了多家銀行的杠杆資金,放棄擴張產(chǎn)能規模,通過對歐美市場的考察分析選擇(zé)向高端(duān)Low-E節能(néng)玻璃轉(zhuǎn)型升級。同時(shí),積極擁抱新經濟,申請成為鄭州商品交易所首批期貨交割廠庫,期貨(huò)市場套保等豐(fēng)富的金融工具使得長利(lì)大大(dà)化解了市場的下行風險(xiǎn)。
“盡管當前市場環境依然嚴峻,但(dàn)長利麵(miàn)臨的壓力小了很多。”王成斌說,在華爾潤(rùn)倒掉後,長利產品憑借優良的品質和低廉的(de)水運成本優勢順(shùn)江而下,迅速填補了巨(jù)頭空出的華東市場。得益於此,2015年末華中玻璃產品售價(jià)與7月份的(de)低點相比反彈高200元/噸之巨,今日黃浦江邊碼頭幾乎每天都可看到發自湖北的玻璃船隻靠港卸貨。 南北價差縮小貿易流(liú)向調整
華爾潤(rùn)產能退出的影響下,其他區域對華東地(dì)區倒灌行動開始湧現(xiàn)。一番調(diào)整後,各區域格局和貿易流向重新穩定,而華中地區無疑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。
“以前華中的玻(bō)璃很難進入華東市場,華爾潤的體量太大(dà)了。”劉政告訴記者,但華爾潤(rùn)破產剛有風聲,華中企業就積極打通渠道,現在華中玻璃經由長江水運迅速補上(shàng),在華(huá)東地區中低端產品市場占有率很(hěn)大(dà),而高端產品部分主要還是旗濱、南玻、台玻等為主。
麵對新騰出的(de)市場空間,華中企業自然受益頗多。但(dàn)在張山(shān)高看來,華中地區玻璃市場的希望不僅僅來源於此,更來(lái)源(yuán)於(yú)正(zhèng)處於上升勢頭的中部經濟。
“從過去10年看,中部地區的經濟是在(zài)上升的,而沿海經濟(jì)是在下滑。”張山高說,10多年前房地產項目都集中在沿(yán)海地區(qū)、北上廣深等一線(xiàn)城市,而(ér)現在二三線城(chéng)市都在搞房地產。“中部(bù)地區人口又多,小縣城裏的二三(sān)十(shí)層樓也蓋得鋪天蓋地的。房產商就是要(yào)玻璃,這使我們的產品銷售(shòu)有了很好的支撐(chēng)。”
據他介紹,以前湖北隻有兩三條線,大(dà)量玻璃不是(shì)往上海就是往廣東發;而現在增加到17條線,其中至少有六七條線銷在了湖北。“但這個(gè)也是不可持續的(de)。”張山(shān)高不無擔心地表示。 “如同當年的廣東,在大量對外貿易支撐下,廣東大量玻璃(lí)深加工企業將各種內地很少生產的玻璃產品賣到了全(quán)世界,帶動了當地的玻璃原片生產和銷售。”張山高分析,“但在過去的5年(nián),這個需求萎縮了,而且萎縮得非常厲害。”在他看來,這其中既(jì)有人民(mín)幣升值的(de)原因,也有我國人工成本優(yōu)勢逐漸消失,投資(zī)者轉投東南(nán)亞各國造成的影響。
廣東當地的浮法(fǎ)玻璃產能近幾年雖有所下降,但是福建旗(qí)濱10條線的產能主要集中銷往廣東(dōng),再加上當(dāng)地玻璃巨頭(tóu)信義剛上4條新線,大企業(yè)資金實力雄厚,短時間內產能不會再有退出。與此同時,廣東的玻璃需求(qiú)卻在(zài)進一步(bù)下滑,受此影響(xiǎng),今(jīn)年(nián)下半年開(kāi)始長利發往廣東的原片(piàn)也(yě)幾乎停擺。
“曆史上玻璃(lí)在南北方(fāng)向上是流動的,沙河往我們這發,我們往廣東那發,現在是沙河(hé)也不往(wǎng)我們這發,我們也(yě)不往廣東發。”張山高(gāo)笑說(shuō),玻璃南北價差縮小的現實下,價差(chà)不足以抵(dǐ)消運費,於(yú)是造成全國玻璃南北銷售半徑更小。
在弘業期貨(huò)分析師(shī)張(zhāng)永鴿(gē)看來,當前產能過剩(shèng)的行(háng)業背景下,轉型升級的最為突出的榜樣來自(zì)華北(běi)地區。為完善其產業(yè)鏈布局和合理發展,沙河廠家將原片玻璃逐步(bù)延伸,大力發展深加工企業,擴(kuò)大了平板玻(bō)璃的銷(xiāo)售範圍,同時也減輕了原片玻璃的銷售壓力,開發多樣化的(de)玻璃產品對提(tí)升華北玻(bō)璃的價格起到有益作(zuò)用。
在華北價格走(zǒu)高(gāo)的作用(yòng)下,原本華(huá)北玻璃對東北市場(chǎng)的(de)大量流入也漸漸停止,轉變為東北玻璃衝擊京津冀地區;與此同時,在打通(tōng)了銷售渠道後,東北玻璃通過船運(yùn)進入到華東、華南甚至(zhì)西南(nán)地區,消化了短時間內河(hé)北迎新集團和廣東信(xìn)義集團為主的大型玻璃企業投產之下(xià)一(yī)度爆發的產能,使得東北地區於2015年下半年一改之前的價格走勢,開始上揚。
但是張山高對於東(dōng)北市場未來的走勢並不看好。他認為,一方麵從人口流動看東北應該呈下降趨勢(shì),進而影(yǐng)響市場需求;另一方麵,由於季節原因玻璃產品生產後要在庫房(fáng)存放(fàng)達四(sì)五個月之久,給企業經(jīng)營帶來壓力。
“這也就(jiù)是為什麽遼寧、內蒙的玻璃廠很難搞下去。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沙河將(jiāng)產品運(yùn)送過去。”張山高說。但是(shì)在東北產能減少的局麵下,仍有(yǒu)不少企業前去投產建線,在(zài)他看來這種策略欠(qiàn)妥。
華爾(ěr)潤事件(jiàn)未波及的當屬西南(nán)市場
西南地區受(shòu)水運困難(nán)、公路運輸成本較高影響,產品流入和流出都(dōu)比較困難,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區域環境(jìng),逢政策利好時企業利潤頗豐。但從2014年6月開始,南玻、信義在西南地區(qū)逐漸上線點火,截至2015年4月,新增玻璃產能接近5000t/d,總產能達到15750t/d。產能的快速增加也引(yǐn)起了業內人(rén)士對於西南可成為“下一個東北”的爭議。
對於巨頭企(qǐ)業接連進入西南地區的(de)行為,王成斌將其解讀為一種迫不得已(yǐ)的選擇(zé)。“過去可(kě)以選(xuǎn)擇到(dào)這裏(lǐ)來(lái),也可以選擇不到這裏(lǐ)來;但現在,自身消(xiāo)化不了,必須要到(dào)這(zhè)裏來。”王成斌說。然而無論如何,西南地區玻璃價(jià)格的持續下滑已(yǐ)經讓業(yè)界看到(dào)了西南市(shì)場的景氣度正在發生變化,外地企業(yè)的進入難度勢必越來越大。